页次:1/373页 共7442篇 20篇/页 |
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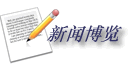 | |
浏览工具:    返回上一页 发布人:patent
我要发布信息 返回上一页 发布人:patent
我要发布信息 | |
| 牛奶盒里放着什么?科学研究就是这样一种猜测 | 2011/10/03 |
| 本报记者 林丹 本报通讯员 尹晓铄 尹炳炎 摄 “绝大部分影响我们对自然界思考方式的科学发现,是难以预测的,技术发明者也不明确新技术在研究事物特性方面的具体应用。现代科技成果很少出自一人之手,它们是整个科技界共同努力和进步的结果……”这个秋天,199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道格拉斯·奥谢罗夫教授来到杭州,为济济一堂的科学爱好者们,揭开“科学进展如何成功”的奥秘。 基础研究其实没有目的 科学的进步,通常都直接受益于人类的发明及技术的出现。但即使在科学上取得进展之后,基础研究也不可能预测人类将要面临的问题。 当你实验的时候,不知道结果如何。这正是科学所带给我们的兴奋点所在。 比如核磁共振。核磁共振技术是由布洛赫和珀塞尔在1946年发明的,他们之所以研究这项技术,是为了弄清磁场中赫兹运动频率的问题。6年后,他们因从事物质核磁共振现象的研究,并创立原子核磁力测量法,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。 当时人们问他们:“核磁共振有什么用处?”布洛赫却说:“这是基础研究,应用范围非常小。” 珀塞尔则回答:“这可以计算磁场的磁力。听起来,这没什么用。” 然而几年后,这个发现很快就成为全球化学实验室中重要的工具之一。 一大批在核磁共振研究领域中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,相继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诺贝尔奖,其中包括1943年、1944年和1952年的物理奖,1991年和2002年化学奖以及2003年的医学奖。 因为通过核磁共振,人类可以获得均匀的磁场,可以通过频率来了解物质在磁场中的运动频率是否和预测的一致。我去过有机化学实验室,每个实验室都有核磁共振设备。 诺奖是对科学的一种庆祝 我认为,人类主要的科学进步,几乎都依赖于较小的一些进步,或其他人所取得的新技术的进展。我的研究中,也一直需要用到核磁共振的研究结果。 在发现固体氦时,我并不知道它是液态的还是固态的,所以就和同事讨论,并参考了他们的意见,做了一个静态的磁场,其中同样使用了核磁共振技术。 1972年4月20日晚上,我在查阅4月17日所取得的一维核磁共振成像(MRI)资料时,发现这种液态氦的研究非常有意思,于是就记下来。凌晨4点,激动不已的我打电话给导师David Lee(戴维·李),把好消息告诉了他。我们的研究成果于1972年秋发表,其中包括如何分开液体及固体核磁共振信号的说明。 我知道,很多人都在技术和观点上为此作出了贡献,回顾我获得诺奖的过程,我可以确定地举例说出20位给我提供重要概念、技术的个人。没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,我都不可能作出这项研究。一个人要想快速进步,必须作广泛的研究,科学家之间也要相互交流,同时也应该花一些时间满足自己的好奇心。我的获奖,其实是站在很多人的肩膀之上。 公平地说,诺贝尔奖应该被看作对科学的一种庆祝,而不是对发现者的奖励。我们和其他获奖者一样,当然是聪明人,但是有很多的聪明人,也同样应该获奖。 高中化学老师是启蒙之师 我父亲是医生,父母亲对子女的教育采取相当开明的方式,让子女们依自己的兴趣发展,从不予干涉。 我从小就对各种事物充满好奇,喜欢拆卸东西,研究其作用原理后,再组装回去。8岁时,我拆了父亲给我的旧相机,花了几个小时把所有的零件洒得满地毯都是,当然,相机从此再也没装回去过。但是父亲对我的这些行径倒是从不以为忤,反而鼓励并引导我的研究精神。 我在家中地下室有一个实验室,虽然许多实验都是有风险的,但父母并没有反对。有一次,我把父亲送的一个礼物拆开,在研究动力的时候,玩具突然爆炸,我被炸得倒在了地板上。
霍克老师有一天带了一个牛奶盒进教室,要大家猜里头放了什么。他说科学研究就像是猜测的过程,你可以摇一摇,听听声音;也可以滚动一下,看看里面的东西如何反应如果里面的东西很顺利地沿着牛奶盒滚动,就可以合理地猜测里面的东西应该是具备圆柱、对称的特性之类。 我们每天做实验,就像向自然询问一个接一个的问题。自然并不告诉你牛奶盒当中有什么东西,所以你要做其他的更多的实验来判定。你可能会经历失败,然后才能了解自然给你的答案。 (本文来源:浙江在线-钱江晚报) | |
 新闻博览
新闻博览 

